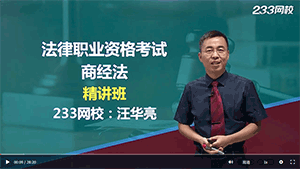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七)条件成否未定时的效力
条件成否未定的状态,德国法上称为“未决期间”。在此状态下,停止条件的消灭时效不起算,权利人处分权能受限制;解除条件则没有这种限制,但在债权行为时应承担在条件成就后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此时也产生不依不正当行为妨害条件成就或否的义务(见前文)。但是,并非合同当事人的其它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例如:次债务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享有债权的第三人)如为妨害行为,也可以产生此拟制效果[30]。不过,如果是无直接利害关系之人(如当事人一方亲友)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使条件成就或不成就,应解为不发生拟制效果。但可依照侵权行为法对该人行使侵权之债请求权[31]
我国台湾和大陆一些学者常常以为,附条件和期限的法律行为赋予了当事人期待权[32],然而,这是错误的。绝大多是情形下,当事人根据附条件的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享有的仅仅是单纯的期待地位,而不是完整的一项权利,与期待权不可同日而语。《德国民法典》第160条[33]也并未赋予当事人任何权利,即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仅仅在条件成就后才产生;同样,条件成就前,当事人也不能处分这种尚未发生的权利。附条件和期限的负担行为是绝对不可能赋予当事人期待权的,但是,对于一部分处分行为,受让人享有期待权。关于期待权,在后面笔者还会谈到。
(八)条件的两个边缘问题
(1)日本民法规定,以实施不法行为作为条件的法律行为无效,约定不为不法行为亦同[34]
对此,其它各国都没有予以效仿采纳,唯有某些学者认为解释上亦应与此相同。因为此种行为表面看上去似乎属于奖励守法,但实际上不为不法行为是每个人在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以之为条件反足以助长不法[35]。实际上,该学者的结论不仅过于仓促草率,理由也完全不具有说服力,令人难以信服。反观史尚宽先生的见解则与其截然有异:如不为不法行为具有反社会性时(如不杀人,则解除赠与),当与日民做同一解释——属无效法律行为。如果不具有反社会性,如“出租此屋于你,若供卖淫之用,则解除合同”,非但无伤淳风美俗,反有助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便不妨使其发生法律效力[36]。这个观点不但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且兼顾社会正义,堪称妥适
(2)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究竟是合同附条件还是物权移转附条件?这个问题在前文讨论法律行为的“分离原则”时已有提及,这里更详细地说明一下:
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分期付款买车或“按揭(mortgage)”买房的交易方式。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其实融资租赁和让与担保的基本原理与此也是一致的)。这时如果将条件认为附在买卖合同本身,则由于条件不成就,买卖合同尚未发生效力,卖方便永远无权请求支付价款(这里不存在一部生效的问题,因为法律行为一旦附有条件,便决定着整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关于这点前面也已经交代了)。所以必须认为此时是在所有权移转的法律行为里附上了一个条件而不是什么买卖合同附条件[37]。这也是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这也又一次告诫我们:对于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一定要区别对待。分离原则并不必然导致抽象原则,对前者没必要抱有太大的成见和戒备心理,只要某种观点能够让我们法律的逻辑体系更具有连贯性和说服力且符合正义观念,便应该予以吸收和借鉴。否则只能犯下类似马克思先生所讥讽的“倒洗澡水时把盆子里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的愚蠢错误了
关于本文的核心部分——法律行为的条件暂告一段落,现在进入本文最后一部分——期待权制度
(一)期待权——德国法系的世纪之争
期待权制度一向是德国法上的热门话题,在同属于德国法系的日本、我国台湾、1990年代以后的我国大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探索。这个概念在德国法上提出的时间很早,据认为首先对这个概念提出系统总结的学者为齐特尔曼教授,他在其著作《国际私法》中设专章对“期待权” (Anwartschaftsrecht)进行了论述,并把“Anwartschaft”和“Wartrecht”融合在一起。从此“期待权”这一概念在德国的民法教科书中被广为使用[38]即便如此,在以抽象思维能力见长的德国学界也长时间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一直以来能够达成的有限共识只有以下几点内容:
(1)期待权并非单纯的期待,单纯期待仅仅是取得权利的机会,而是否能取得权利是不确定的,因此也不受法律保护,例如,子女对父母财产未来的继承权,在父母死亡前,仅仅是单纯的期待,因为尚不知道子女在父母死亡时是否仍然生存,所以这种期待是无法得到保护的;
(2)期待权也不是完整的权利,因为其并不符合某种权利的构成要件
(3)期待权是介于权利与期待之间的一种状态
(4)期待权人已经实现了部分权利构成要件,这是指权利主体已确定,并且所期待的特定利益的内容或范围已经确定。如为对人权,则义务主体也应已确定[39]
能达成以上共识,不得不谓难能可贵。然而,这些对期待权的看法与其说是构成要件,还不如说是对期待权的大致描述,尤其对具体的期待权类型仍然无法通过以上判断方法得以确定下来。可以说:如果把“期待权”比做是一幅油画,那种程度的认识充其量只完成了用铅笔勾画轮廓的步骤,至于这画到底最终是什么模样,还处于尚未可知的状况。
早年留学德国、师从名儒拉伦茨氏、对德国法有深入研究的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一番颇为痛苦的、没有得出实质结论的思量以后,在1970年代曾经仰天长叹道:“对其作一确定之界说,恐难周全,最好的方法系观察判例学说上所承认各类型期待权之性质,分析其共同特征”[40]
需要澄清的是:我对王教授之学识渊博深为景仰,一向心存敬意,不怀偏见。只是在此处,他又一次犯了那个“以一种不确定取代另一种不确定”的错误,说难听点就是推卸责任,颇有点企图蒙混过关的感觉。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将错误归咎于他的身上,毕竟德国法学家花了一个世纪还处于争论的问题,又怎么是一个只在德国呆了几年的中国留学生能轻而易举地“摆平”呢?果真如此,那德国法学就真可谓人才凋零、江河日下了。